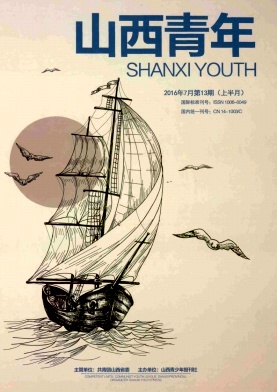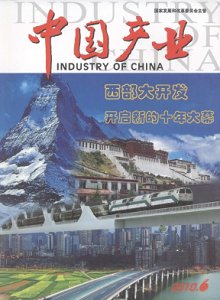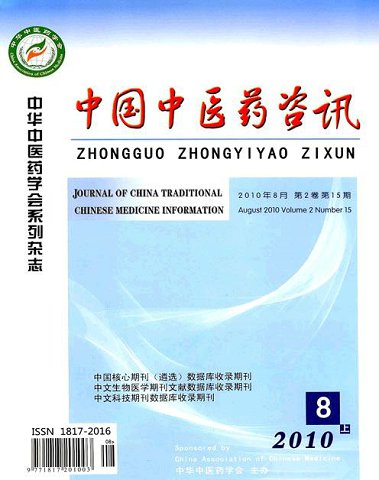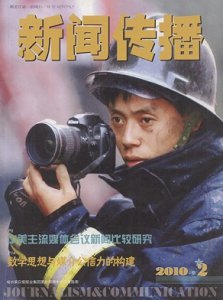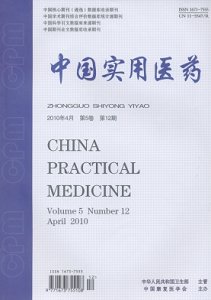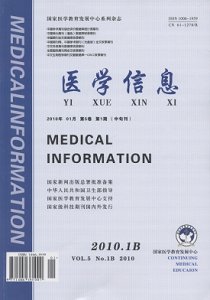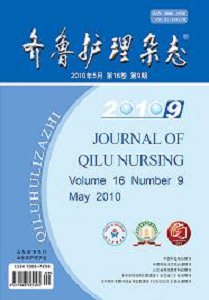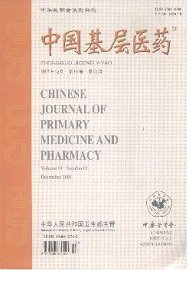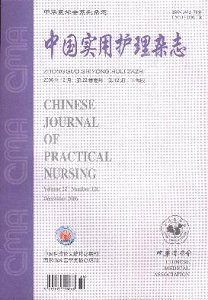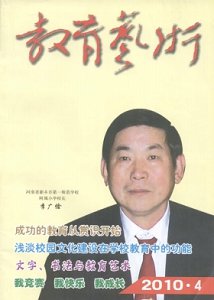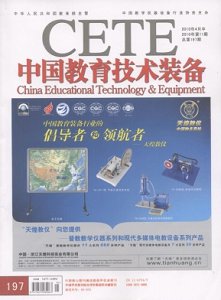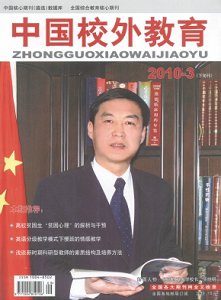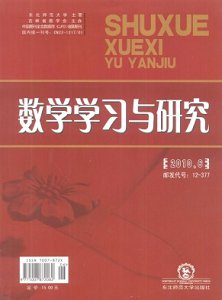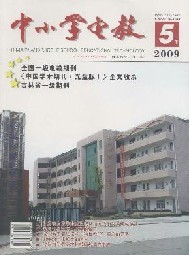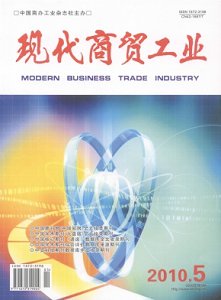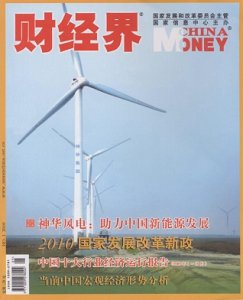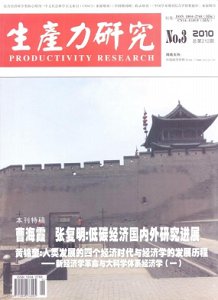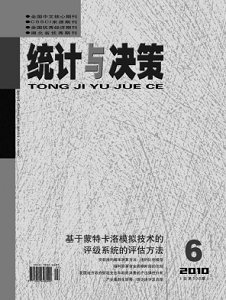论关于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身体主体意识
论文摘要:女性的身体主体意识,是指女性对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力意识,也即女性对自我身体的欣赏、支配、享受的自由意志。中国当代的都市女性写作正是侧重从“赞美身体”、“支配身体”、“享受身体”等几个层面,对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及身体主体意识进行前所未有的审美表现和文化透视。作为一种性别意识鲜明的“性别写作”亦或“身体写作”,都市女作家对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审美表现和张扬,必将极大促动女性久被遮蔽、禁锢且多灾多难的身体走向解放和自由,并最终整体地促进和提升女性的性别觉醒和精神成长。
论文关键词: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身体主体意识.
人人都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身体,身体构成了个体生命和自我意识最为直接的现实。“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涵义中最为明确的部分。很少人会对躯体整体或局部的主权归属表示疑问。从鼻子、胳膊、大腿到完整的七尺之躯,这一切无不属于——同时也构成了——特定个体。这无形地巩固了躯体自主、独立、完整的观念。然而,在人类漫长的性别历史发展中,由于男权社会长期严酷的性别压抑和性别禁锢,女性被推向对象化存在(性别压迫对象、性别审美对象、性别欲望对象等)的不平等的性别地位,其身体也终究难逃多灾多难的性别厄运,遭受了普遍而深刻的性别异化,诸如“贞操节烈”、“三寸金莲”、“燕瘦环肥”等等都是女性遭受身体异化和性别迫害的铁证,其身体的自主、独立、完整的观念也即身体的主体意识自然也早已丧失殆尽。女性在经受这种长期的“身体异化”之后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正如法国著名女权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曾深刻揭示的:“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也即是说,女性的身体不仅丧失了自我主体性,还被严重地弱化、丑化和妖魔化——“女性的身体美丽、神秘、吸引人但又不洁、危险、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它既是快感和温存的来源,又令人恐惧和厌恶,多是魔鬼和邪恶的化身E](。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成长,得益于近现代以来日益发展的女权主义思潮的大力促动和深刻影响。伴随着“五四”以来女权思想的不断发育和成长,时至今日,以都市女性为主体的一代新女性,业已建构起颇具现代、先锋和另类色彩的性别观念及其身体主体意识。在诸多新潮都市女作家笔下,新女.陛的这种身体主体意识得到了艺术而审美的文学呈现和性别阐释。
阐释之一,赞美身体。“身体是件神圣的衣裳,是你的最初与最后的衣裳,是你进入生命亦是你告别生命之地,故而你应以爱敬的心对待它,以喜悦和畏惧,以感恩。”这是台湾当代实力派女作家朱天文在其著名作品《荒人手记》中盛赞“身体”的一段耐人寻味的优美文字。对身体尤其女性身体的诗性刻画和由衷赞美,不论在思想开放、文化发达的台湾,还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大陆,均已成为都市女性写作的一种近乎普遍的创作现象,透过女作家笔下那些从容、优雅而充满生命活力的女性身体形象,令人真切地感受到当代新女性那种饱满而蓬勃的生命意识和自我主体意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较早对女性的身体进行审美表现的,首推诗歌和散文。诗歌方面如林祁的《浴后》:“全身镜里走来女娲/走来夏娃/走来我/直勾勾地望着我/收腹,再收腹/乳峰突起/我抚摸我温情似海/我看到/地狱之门/充满诱惑/哦,给我一百次生命/我只愿切实地/做一回女人。”再如伊蕾的《我的肉体》:“我是浅色的云/铺满你坚硬的陆地/双腿野藤一样缠绕/乳房百合一样透明/脸盘儿桂花般清香/头发的深色枝条悠然荡漾/我的眼睛饱含露水/打湿了你的寂寞/大海的激情是有边沿的/而我没有边沿/走遍世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纯洁的身体。”直到今天,对女性身体美的关注和张扬仍然是女性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如郁雯的《肉体》:“肉体,我凝望着你/一个纯白精致的尤物/你坐着、走着、跑着、笑着/我凝望着你,肉体,美丽的尤物/你是简单的、自然的、饱满的、盛开的花朵。”在女诗人所营造的浪漫而激情洋溢的诗歌氛围中,女性的身体健康而纯净,唯美而迷人。散文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应属叶梦的《羞女山》,这篇散文堪称女作家表现女性身体美的绝唱、讴歌女性生命意识的赞美诗:“蓦地,我惊呆了。对岸的羞女山,什么时候变作了一尊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少女浮雕?那斜斜地靠着陡峭的山岗,仰面青山躺着的,不就是羞女吗?她那线条分明的下颌高高翘起,瀑布般的长发软软地飘垂,健美的双臂舒展地张开,匀称的长腿,两臂微微弯曲着,双脚浸人清清的江流。还有,她那软细的腰,稍稍隆起的小腹和高高凸出的乳峰,在暖融融的斜照的夕阳下,羞女‘身体’的一切线条都是那样地柔和,那样地逼真,那样地凸现,那样地层次分明:活脱脱一个富有生气的少女,赤裸裸地酣睡在那夕阳斜照的山岗。我似乎感觉到了她身体的温度,看得见她呼吸的起伏。我被羞女全美的‘体态’震慑了,心灵沉浸在一种莫名的颤栗之中。我感叹造化的伟力”与世俗和传说中羞女山的尴尬形象大异其趣,叶梦笔下的羞女山是那样的美轮美奂,栩栩如生,昭示了当代新女性不羁的生命个性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都市女作家为主的女性小说创作开始突出表现女性的生命意识,对女性身体的诗性描绘逐渐成为创作上的热点和日趋普遍的审美追求。她们有的侧重刻画女性身体浑朴天成、风情万种的自然美,如海莲的《巢恋》:“她(江雪)舒展着饱满的躯体,像一片春天嫩绿的叶子,秀美的脸庞在柔和的光线下娇艳、妩媚。江雪的形体是东方女性孕育的花朵,洁白的肤色在灯光下闪着圣洁的光亮。芳香从体内散发出来,那是水仙花的清淡,是白玫瑰的芬芳。”也有的注重彰显女性身体的青春华彩、生命活力及其独有的艺术美质,如赵凝的《体香》:“她的身体具有一种完美的比例,修长,丰满,结实,我从没见过像巫美丽这么美的女人体。她动起来,身上的牡丹花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那些妖冶迷人的花,每一朵都像真的。女人摆出女人的姿势,花朵摆出花朵的姿势,它们就像是相互独立似的,独立而又诱人,我仿佛闻到了花朵芬芳的气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市女作家对女性身体的由衷赞美与讴歌,擦亮了女性世界尘封已久的性别意识和身体意识,张扬了女性世界独特的性别审美逻辑和身体美学追求,有力地消解了男权社会及其性别文化传统对女性身体贯有的不良想象和审美偏见,构成了女性写作及其性别诗学建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阐释之二,支配身体。在人类漫长的两性生活及其性别关系中,女性及其身体一直被异化为异己之物,从来都不属于自己,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之说就是明证。因此,当都市女作家笔下的先锋女性喊出“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的时代强音时,表明一个女性身体挣脱禁锢回归自我的新时代正在到来,也表征着当代新女性的性别革命、身体革命已进入到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女性逐渐获得身体支配权的崭新时代里,两性的性别关系、性别秩序要重新调整和定位,两性的性别价值尤其两性的身体价值必须重估。在当代都市女作家表现女性的身体革命,表现女性在两性复杂的情感、欲望和利益关系中如何支配身体、主宰身体的诸多文学作品中,缪永的《驶出欲望街》,可谓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表面上看,这部作品不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深圳这个新兴都市里的富人包养“二奶”的故事。但作为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张志菲决不是一般的“二奶”,她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强烈女权主义思想倾向的时代新潮女性。在作品中,张志菲的女权思想倾向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她具有强烈的身体主体意识。正如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著名女权主义学者李银河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所强调的:“支配自己的身体是每个人的权利”,张志菲也认为自己与富商韦昌同居三个月赚得十五万,是自己个人的权利,也即自己支配、行使自己身体的权利;并且,她认为这种行为并无不妥:“就当和他结婚3个月又离婚了,一个女人结了婚,靠丈夫一辈子,和她跟韦昌3个月有什么本质不同呢?以婚姻或是现金形式讨价,难道还有什么差别?”其次,她具有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与只图卖身投靠、甘做“笼中鸟”的一般“二奶”不同,张志菲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她坚执的人格独立意识。这种人格独立意识,可以鲜明地从她理智拒绝韦昌的狂热求婚中凸显出来:“就算做了他的妻子,她的下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不是跟现在一样,吃他的用他的吗?眼睁睁地看着他朝秦暮楚,到时候,要再生了孩子给他,她的一辈子都在他手里了,纵然繁荣,纵然富贵,可不是她想要的生活。总有一天,她会比他们都好。”显而易见,由于张志菲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女权主义性别内涵和价值取向。
阐释之三,享受身体。所谓享受身体,即对身体感官及其情欲及性爱满足的追求和享受。它理应是人类个体都该充分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在男权文化制度的长期约束和挤压之下,女性的这种基本权利几乎丧失殆尽。这正如国内著名性别文化研究专家孙绍先先生深刻指出的:“性权力是指一个人自主支配其身体的权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性对象与性行为方式的权力;二是拒绝性骚扰与性侵犯的权力。显然这应当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权力,没有必要由外部授权,也不容外部剥夺。然而在世界各种类型的父权社会里,剥夺限制女性的性权力却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实际上,对女性身体的禁锢,对女性性权力的剥夺,一直是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制度和文化传统,而诸如当代都市女性写作中,女性对身体禁锢的自我解放以及女性对身体感官快乐的大胆追求,无疑已构成了对男权社会及其性别制度和文化传统最直接的冒犯和最有力的解构。这种冒犯和解构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其一,作为审美主体的女性,不仅可以将自己的躯体之美公然地展示给异性,还能够直接面对异性的躯体之美,而女性的这些行为一直是被男权文化视为伤风败俗而遭禁忌的。这种“身体”对于女性的“禁忌”,正如新锐女作家王小柔在其日记体小说《你别碰我:一个女生的“青春”日记》中,借女主人公之口所发出的困惑和感慨:“我一直不明白,女生的身体被男生偷窥是吃亏,看到了男生的身体也吃亏,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遭到这样的事情女生永远都是受害者呢?”与仍然困惑于传统“身体禁忌”的这类“女生”不同,都市女作家笔下的当代新潮女性早已习惯于坦然地欣赏和享受异性的躯体之美,试看先锋女作家万芳的小说《我是谁的谁是谁》中的一段描写:“他的身材十分完美,肩膀宽阔,腹部平坦,臀部紧凑,双腿笔直,他很为自己的身材骄傲,也很喜欢被我注视”再看实力派女作家张抗抗在小说《情爱画廊》中的一段描写:“她抚摩着他发达光滑的胸肌,也在细细欣赏周由的男性人体阳刚之美。她知道那是胸大肌、肱二头肌和胸锁乳突肌,它们富有弹性地鼓胀着,饱含着男性的诱惑、充满了枭雄般的力量。”在都市女作家笔下诸如此类且越来越多的优美文学段落里,已全然看不到“身体禁忌”带给女性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创伤,有的只是男性美体奉献给女性的视觉盛宴和感官狂欢。其二,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能够自主地充分地追求和享受两性和谐、完满的性爱之美。在女作家的这类充溢着勃勃激情和款款温馨的文字里,令人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曼妙、青春的激情和生活的美好,比如:“厚厚的窗帘挡住春天的艳丽。我们躺在~IIJL,两具白色的生气勃勃的身体缠绕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存在的价值,是在一个瞬间强烈地呈现出来。活着真好,年轻真好,我珍爱着自己。原来,活生生的一切都是单纯的。我们焦灼地互相探寻,用激烈的情欲消融对方,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的身上共同隐藏着最原始的野性。”(唐颖《丽人公寓》)再如:“欲,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是对男人女人生命力的一种检验。身为女人,拥有青春,她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享受生命的机会的。从初中开始,她就和她喜欢的男人约会做爱,从两情的交合中体会肉体带给她的愉悦和快乐。在这样的时刻,她为自己生为女人而感到自豪在欲望面前,男人女人都是平等的。”(黄玲《孽红》)。不仅如此,在思想更为前卫的先锋女性看来,爱与性、情与欲应该是可以分开的,更突出了她们主动追求身体快乐与情欲满足的坚定与执着:“在很多思想解放了的女人眼里,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她们会说:爱与欲分开并不与追求纯洁人生的态度抵触,一天一天消耗着你生命的日常生活引导着女人的直觉与意愿,她们寻找任何一种能使她们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她们把打开生活秘密的钥匙放在枕头底下,她们比50年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前的女性多了美貌,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类别的新高潮。”(卫慧《上海宝贝》)客观地看,新潮女性的这种爱与性分离的另类性爱方式及其价值取向,在当下社会的两性交往中已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某种意义上,这种另类的性爱追求,不仅构成了对传统性别体制及其性爱伦理的冒犯和解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通过女性的身体解放,深刻唤醒了女性久被遮蔽、压抑的自我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极大促进了女性的性别觉醒和精神成长。
显然,作为一种性别意识鲜明、女权立场坚定的“性别写作”亦或“身体写作”,都市女作家对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文学关照和审美表现,具有确定无疑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性别文化重建的意义。但毋庸讳言,都市女性的这种“身体写作”至今一直处于被严重误读、误解的尴尬境地。它原本澄明、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因此而变得隐晦而暖昧,且孳生出太多的是是非非,早已演化为一种争议不断、影响广泛的复杂文学、文化现象。“身体写作”之所以如此备受争议,频遭指责,个中原委,正如新锐女权主义文化学者张念所一针见血地揭露和分析的那样:“身体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色情。而色情也被一厢情愿地理解为暴露指数的攀升,因为暴露和无耻有关。正如集权主义的神秘和遮掩相关一样,为呈现身体真相的暴露,就是解除身体暴政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遮掩比暴露无耻上千倍。这种力透纸背、人木三分的性别阐释和文化批判,无疑是对女作家“身体写作”现象的最有深度的理解和最具力度的辩护。事实上,都市女作家以解除身体暴政、建构女性身体主体意识为历史使命的“身体写作”,从没有淹没在众声喧哗的误读、误解之中,它一直以文学先锋的姿态在传统文化的禁忌中奔突;在性别解放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必将会重估其丰厚的文学实绩和突出的文化贡献。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5389037508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
网址: 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
论文关键词: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身体主体意识.
人人都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与众不同的身体,身体构成了个体生命和自我意识最为直接的现实。“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秩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涵义中最为明确的部分。很少人会对躯体整体或局部的主权归属表示疑问。从鼻子、胳膊、大腿到完整的七尺之躯,这一切无不属于——同时也构成了——特定个体。这无形地巩固了躯体自主、独立、完整的观念。然而,在人类漫长的性别历史发展中,由于男权社会长期严酷的性别压抑和性别禁锢,女性被推向对象化存在(性别压迫对象、性别审美对象、性别欲望对象等)的不平等的性别地位,其身体也终究难逃多灾多难的性别厄运,遭受了普遍而深刻的性别异化,诸如“贞操节烈”、“三寸金莲”、“燕瘦环肥”等等都是女性遭受身体异化和性别迫害的铁证,其身体的自主、独立、完整的观念也即身体的主体意识自然也早已丧失殆尽。女性在经受这种长期的“身体异化”之后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正如法国著名女权主义学者埃莱娜·西苏曾深刻揭示的:“这身体曾经被从她身上收缴去,而且更糟的是这身体曾经被变成供陈列的神秘怪异的病态或死亡的陌生形象,这身体常常成了她的讨厌的同伴,成了她被压制的原因和场所。也即是说,女性的身体不仅丧失了自我主体性,还被严重地弱化、丑化和妖魔化——“女性的身体美丽、神秘、吸引人但又不洁、危险、具有欺骗性和破坏性,它既是快感和温存的来源,又令人恐惧和厌恶,多是魔鬼和邪恶的化身E](。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成长,得益于近现代以来日益发展的女权主义思潮的大力促动和深刻影响。伴随着“五四”以来女权思想的不断发育和成长,时至今日,以都市女性为主体的一代新女性,业已建构起颇具现代、先锋和另类色彩的性别观念及其身体主体意识。在诸多新潮都市女作家笔下,新女.陛的这种身体主体意识得到了艺术而审美的文学呈现和性别阐释。
阐释之一,赞美身体。“身体是件神圣的衣裳,是你的最初与最后的衣裳,是你进入生命亦是你告别生命之地,故而你应以爱敬的心对待它,以喜悦和畏惧,以感恩。”这是台湾当代实力派女作家朱天文在其著名作品《荒人手记》中盛赞“身体”的一段耐人寻味的优美文字。对身体尤其女性身体的诗性刻画和由衷赞美,不论在思想开放、文化发达的台湾,还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的中国大陆,均已成为都市女性写作的一种近乎普遍的创作现象,透过女作家笔下那些从容、优雅而充满生命活力的女性身体形象,令人真切地感受到当代新女性那种饱满而蓬勃的生命意识和自我主体意识。新时期文学创作中较早对女性的身体进行审美表现的,首推诗歌和散文。诗歌方面如林祁的《浴后》:“全身镜里走来女娲/走来夏娃/走来我/直勾勾地望着我/收腹,再收腹/乳峰突起/我抚摸我温情似海/我看到/地狱之门/充满诱惑/哦,给我一百次生命/我只愿切实地/做一回女人。”再如伊蕾的《我的肉体》:“我是浅色的云/铺满你坚硬的陆地/双腿野藤一样缠绕/乳房百合一样透明/脸盘儿桂花般清香/头发的深色枝条悠然荡漾/我的眼睛饱含露水/打湿了你的寂寞/大海的激情是有边沿的/而我没有边沿/走遍世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纯洁的身体。”直到今天,对女性身体美的关注和张扬仍然是女性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如郁雯的《肉体》:“肉体,我凝望着你/一个纯白精致的尤物/你坐着、走着、跑着、笑着/我凝望着你,肉体,美丽的尤物/你是简单的、自然的、饱满的、盛开的花朵。”在女诗人所营造的浪漫而激情洋溢的诗歌氛围中,女性的身体健康而纯净,唯美而迷人。散文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应属叶梦的《羞女山》,这篇散文堪称女作家表现女性身体美的绝唱、讴歌女性生命意识的赞美诗:“蓦地,我惊呆了。对岸的羞女山,什么时候变作了一尊充盈于天地之间的少女浮雕?那斜斜地靠着陡峭的山岗,仰面青山躺着的,不就是羞女吗?她那线条分明的下颌高高翘起,瀑布般的长发软软地飘垂,健美的双臂舒展地张开,匀称的长腿,两臂微微弯曲着,双脚浸人清清的江流。还有,她那软细的腰,稍稍隆起的小腹和高高凸出的乳峰,在暖融融的斜照的夕阳下,羞女‘身体’的一切线条都是那样地柔和,那样地逼真,那样地凸现,那样地层次分明:活脱脱一个富有生气的少女,赤裸裸地酣睡在那夕阳斜照的山岗。我似乎感觉到了她身体的温度,看得见她呼吸的起伏。我被羞女全美的‘体态’震慑了,心灵沉浸在一种莫名的颤栗之中。我感叹造化的伟力”与世俗和传说中羞女山的尴尬形象大异其趣,叶梦笔下的羞女山是那样的美轮美奂,栩栩如生,昭示了当代新女性不羁的生命个性和强烈的自我意识。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都市女作家为主的女性小说创作开始突出表现女性的生命意识,对女性身体的诗性描绘逐渐成为创作上的热点和日趋普遍的审美追求。她们有的侧重刻画女性身体浑朴天成、风情万种的自然美,如海莲的《巢恋》:“她(江雪)舒展着饱满的躯体,像一片春天嫩绿的叶子,秀美的脸庞在柔和的光线下娇艳、妩媚。江雪的形体是东方女性孕育的花朵,洁白的肤色在灯光下闪着圣洁的光亮。芳香从体内散发出来,那是水仙花的清淡,是白玫瑰的芬芳。”也有的注重彰显女性身体的青春华彩、生命活力及其独有的艺术美质,如赵凝的《体香》:“她的身体具有一种完美的比例,修长,丰满,结实,我从没见过像巫美丽这么美的女人体。她动起来,身上的牡丹花开始大口大口地呼吸,那些妖冶迷人的花,每一朵都像真的。女人摆出女人的姿势,花朵摆出花朵的姿势,它们就像是相互独立似的,独立而又诱人,我仿佛闻到了花朵芬芳的气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市女作家对女性身体的由衷赞美与讴歌,擦亮了女性世界尘封已久的性别意识和身体意识,张扬了女性世界独特的性别审美逻辑和身体美学追求,有力地消解了男权社会及其性别文化传统对女性身体贯有的不良想象和审美偏见,构成了女性写作及其性别诗学建构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阐释之二,支配身体。在人类漫长的两性生活及其性别关系中,女性及其身体一直被异化为异己之物,从来都不属于自己,所谓“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之说就是明证。因此,当都市女作家笔下的先锋女性喊出“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样的时代强音时,表明一个女性身体挣脱禁锢回归自我的新时代正在到来,也表征着当代新女性的性别革命、身体革命已进入到一个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女性逐渐获得身体支配权的崭新时代里,两性的性别关系、性别秩序要重新调整和定位,两性的性别价值尤其两性的身体价值必须重估。在当代都市女作家表现女性的身体革命,表现女性在两性复杂的情感、欲望和利益关系中如何支配身体、主宰身体的诸多文学作品中,缪永的《驶出欲望街》,可谓最具代表性的一部。表面上看,这部作品不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深圳这个新兴都市里的富人包养“二奶”的故事。但作为这个故事的女主人公,张志菲决不是一般的“二奶”,她实际上是一个具有强烈女权主义思想倾向的时代新潮女性。在作品中,张志菲的女权思想倾向突出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她具有强烈的身体主体意识。正如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著名女权主义学者李银河在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所强调的:“支配自己的身体是每个人的权利”,张志菲也认为自己与富商韦昌同居三个月赚得十五万,是自己个人的权利,也即自己支配、行使自己身体的权利;并且,她认为这种行为并无不妥:“就当和他结婚3个月又离婚了,一个女人结了婚,靠丈夫一辈子,和她跟韦昌3个月有什么本质不同呢?以婚姻或是现金形式讨价,难道还有什么差别?”其次,她具有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与只图卖身投靠、甘做“笼中鸟”的一般“二奶”不同,张志菲身上最可贵的品质在于她坚执的人格独立意识。这种人格独立意识,可以鲜明地从她理智拒绝韦昌的狂热求婚中凸显出来:“就算做了他的妻子,她的下场又能好到哪里去呢?不是跟现在一样,吃他的用他的吗?眼睁睁地看着他朝秦暮楚,到时候,要再生了孩子给他,她的一辈子都在他手里了,纵然繁荣,纵然富贵,可不是她想要的生活。总有一天,她会比他们都好。”显而易见,由于张志菲这一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非同一般的女权主义性别内涵和价值取向。
阐释之三,享受身体。所谓享受身体,即对身体感官及其情欲及性爱满足的追求和享受。它理应是人类个体都该充分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但在男权文化制度的长期约束和挤压之下,女性的这种基本权利几乎丧失殆尽。这正如国内著名性别文化研究专家孙绍先先生深刻指出的:“性权力是指一个人自主支配其身体的权力。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性对象与性行为方式的权力;二是拒绝性骚扰与性侵犯的权力。显然这应当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自然权力,没有必要由外部授权,也不容外部剥夺。然而在世界各种类型的父权社会里,剥夺限制女性的性权力却是我们这个世界里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实际上,对女性身体的禁锢,对女性性权力的剥夺,一直是男权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制度和文化传统,而诸如当代都市女性写作中,女性对身体禁锢的自我解放以及女性对身体感官快乐的大胆追求,无疑已构成了对男权社会及其性别制度和文化传统最直接的冒犯和最有力的解构。这种冒犯和解构至少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其一,作为审美主体的女性,不仅可以将自己的躯体之美公然地展示给异性,还能够直接面对异性的躯体之美,而女性的这些行为一直是被男权文化视为伤风败俗而遭禁忌的。这种“身体”对于女性的“禁忌”,正如新锐女作家王小柔在其日记体小说《你别碰我:一个女生的“青春”日记》中,借女主人公之口所发出的困惑和感慨:“我一直不明白,女生的身体被男生偷窥是吃亏,看到了男生的身体也吃亏,为什么无论什么时候遭到这样的事情女生永远都是受害者呢?”与仍然困惑于传统“身体禁忌”的这类“女生”不同,都市女作家笔下的当代新潮女性早已习惯于坦然地欣赏和享受异性的躯体之美,试看先锋女作家万芳的小说《我是谁的谁是谁》中的一段描写:“他的身材十分完美,肩膀宽阔,腹部平坦,臀部紧凑,双腿笔直,他很为自己的身材骄傲,也很喜欢被我注视”再看实力派女作家张抗抗在小说《情爱画廊》中的一段描写:“她抚摩着他发达光滑的胸肌,也在细细欣赏周由的男性人体阳刚之美。她知道那是胸大肌、肱二头肌和胸锁乳突肌,它们富有弹性地鼓胀着,饱含着男性的诱惑、充满了枭雄般的力量。”在都市女作家笔下诸如此类且越来越多的优美文学段落里,已全然看不到“身体禁忌”带给女性的心理阴影和精神创伤,有的只是男性美体奉献给女性的视觉盛宴和感官狂欢。其二,作为欲望主体的女性,能够自主地充分地追求和享受两性和谐、完满的性爱之美。在女作家的这类充溢着勃勃激情和款款温馨的文字里,令人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的曼妙、青春的激情和生活的美好,比如:“厚厚的窗帘挡住春天的艳丽。我们躺在~IIJL,两具白色的生气勃勃的身体缠绕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存在的价值,是在一个瞬间强烈地呈现出来。活着真好,年轻真好,我珍爱着自己。原来,活生生的一切都是单纯的。我们焦灼地互相探寻,用激烈的情欲消融对方,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的身上共同隐藏着最原始的野性。”(唐颖《丽人公寓》)再如:“欲,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是对男人女人生命力的一种检验。身为女人,拥有青春,她是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享受生命的机会的。从初中开始,她就和她喜欢的男人约会做爱,从两情的交合中体会肉体带给她的愉悦和快乐。在这样的时刻,她为自己生为女人而感到自豪在欲望面前,男人女人都是平等的。”(黄玲《孽红》)。不仅如此,在思想更为前卫的先锋女性看来,爱与性、情与欲应该是可以分开的,更突出了她们主动追求身体快乐与情欲满足的坚定与执着:“在很多思想解放了的女人眼里,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她们会说:爱与欲分开并不与追求纯洁人生的态度抵触,一天一天消耗着你生命的日常生活引导着女人的直觉与意愿,她们寻找任何一种能使她们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她们把打开生活秘密的钥匙放在枕头底下,她们比50年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前的女性多了美貌,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类别的新高潮。”(卫慧《上海宝贝》)客观地看,新潮女性的这种爱与性分离的另类性爱方式及其价值取向,在当下社会的两性交往中已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某种意义上,这种另类的性爱追求,不仅构成了对传统性别体制及其性爱伦理的冒犯和解构,更重要的还在于,它通过女性的身体解放,深刻唤醒了女性久被遮蔽、压抑的自我主体意识和生命意识,极大促进了女性的性别觉醒和精神成长。
显然,作为一种性别意识鲜明、女权立场坚定的“性别写作”亦或“身体写作”,都市女作家对女性身体主体意识的文学关照和审美表现,具有确定无疑的文学审美价值和性别文化重建的意义。但毋庸讳言,都市女性的这种“身体写作”至今一直处于被严重误读、误解的尴尬境地。它原本澄明、丰富的文学、文化内涵因此而变得隐晦而暖昧,且孳生出太多的是是非非,早已演化为一种争议不断、影响广泛的复杂文学、文化现象。“身体写作”之所以如此备受争议,频遭指责,个中原委,正如新锐女权主义文化学者张念所一针见血地揭露和分析的那样:“身体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色情。而色情也被一厢情愿地理解为暴露指数的攀升,因为暴露和无耻有关。正如集权主义的神秘和遮掩相关一样,为呈现身体真相的暴露,就是解除身体暴政的第一步,在这个意义上,遮掩比暴露无耻上千倍。这种力透纸背、人木三分的性别阐释和文化批判,无疑是对女作家“身体写作”现象的最有深度的理解和最具力度的辩护。事实上,都市女作家以解除身体暴政、建构女性身体主体意识为历史使命的“身体写作”,从没有淹没在众声喧哗的误读、误解之中,它一直以文学先锋的姿态在传统文化的禁忌中奔突;在性别解放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必将会重估其丰厚的文学实绩和突出的文化贡献。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5389037508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
网址: 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