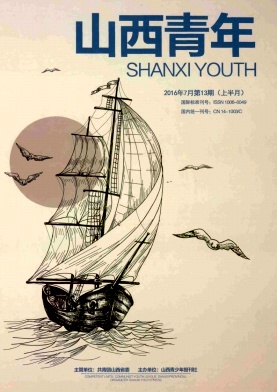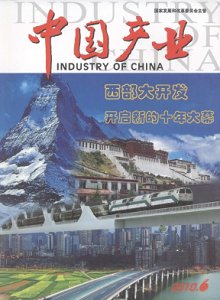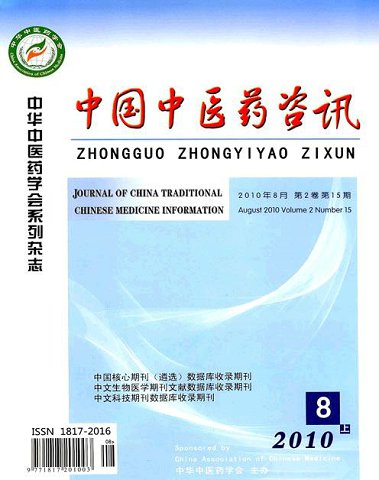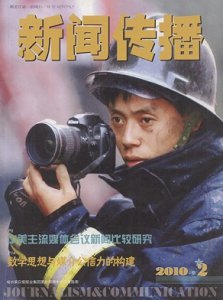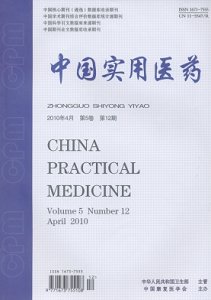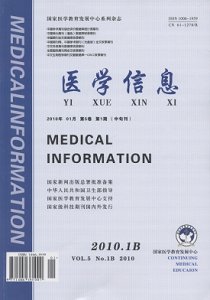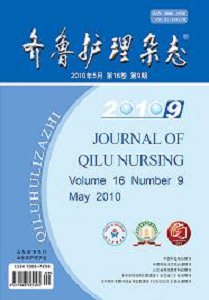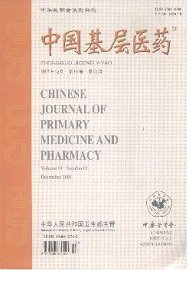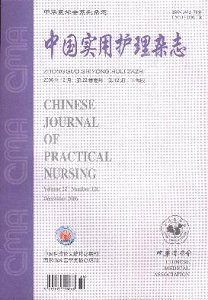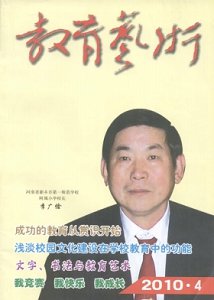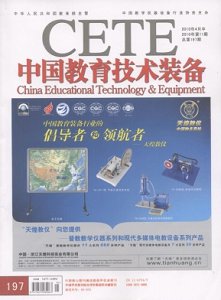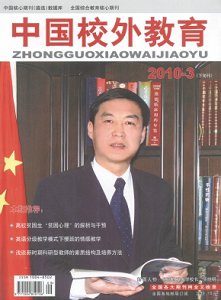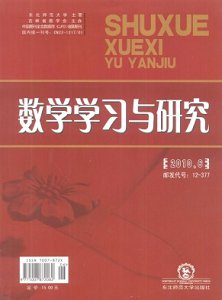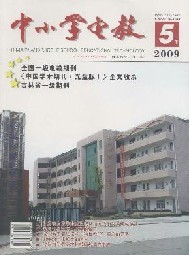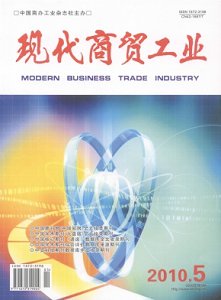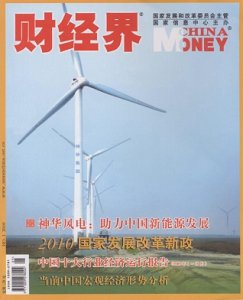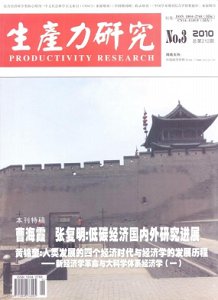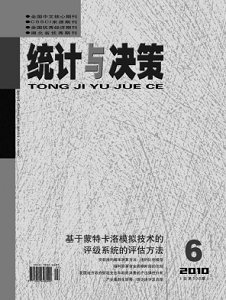浅谈中国当代都市女性写作的性别主体意识
论文摘要:中国当代都市女性的性别写作其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取向,在于对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积极建构和大力促动。一般而言,女性的性别主体意识主要指在男权文化制约下的各种性别关系中,女性已不甘于传统性别文化派给自己的各种屈辱性别身份,而力图通过性别抗争和文化重建,恢复与男性同等的主体地位和人格尊严。都市女性写作对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凸显和张扬,昭示了当代新潮女性具有性别革命意义的精神觉醒和思想成长。
作为一种特别关注当代都市社会中各种复杂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的“性别”文学,中国当代的都市女性写作因其突出的性别视角和明显的反男权叙事,而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女性主义思想、艺术新质的复杂文学现象。与充满男权意识的传统、正统文学或主流文学的价值取向大异其趣,都市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整体上看,都市女性写作的价值追求最主要体现在对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积极建构上,女性的性别主体意识无疑已构成了都市女性写作的价值体系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部分。所谓“性别主体意识”,是指在都市女作家笔下的各种性别关系中,女性已不再甘心于男权社会及其性别文化传统强行派定的“次性”、“他者”、“第二性”等屈辱的性别身份,而是力图通过性别抗争和性别革命恢复与男性同等的主体性地位和人格尊严。都市女性写作的这种性别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其所塑造的当代新潮女性与传统女性判然有别,与传统观念格格不人的情爱主体意识以及婚姻意识等诸多层面,凸显了充分浸淫现代女权思想的一代新女性具有性别革命意义的精神觉醒和思想成长。
一、情爱主体:“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情爱”,是人类两性最基本的性别关系之一,它构成了人类两性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内容,它尤其是青年男女温馨浪漫、最富生命激情的精神生活内容。然而,在充满性别歧视的男权文化传统及其性别体制的强力约束之下,女性“爱”的资格、权力和机会几乎被剥夺殆尽。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也很难说女性已经完全享有了性别平等意义上的“爱”的权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都市女作家笔下的那些新潮女性其前卫的情爱观念以及对情爱的大胆追求和与传统相悖的另类情爱生活方式,才充分显现出颇具反叛色彩的性别觉醒和情爱革命的尖锐锋芒。
首先,情爱观念的根本转变,成为当代新潮女性性别觉醒和情爱革命最为重要的关键步骤。在当代都市女作家所塑造的诸多新潮女性人物群像中,这种情爱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这些新潮女性一改传统女性对待情爱的被动心态,大胆、主动地追求心中的理想爱情,有的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典型的如王安忆在其著名的“三恋”之一的《荒山之恋》(原载《十月》1986年第4期)中塑造的金谷巷女孩。作为有夫之妇,金谷巷女孩不顾世俗流言,疯狂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但最后二人终究难敌来自世俗社会方方面面的强大压力,双双殉情。作为这一爱情悲剧的主角,金谷巷女孩最令人喟叹、感佩的,也许并不是她的最后殉情,而是她积极主动、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的叛逆性格和执着精神。其二是这些新潮女性一改传统女性的从属、依附心理,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情爱自主、情爱平等意识,这正如当代著名女诗人舒婷在其名作《致橡树》中所宣告的那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女性在两性情爱生活中的这种凸显的自主、平等意识,无疑表征着女性人格意识、尊严意识也即性别主体意识的高度觉醒。其三是新潮女性勇于改写“男人好女色”的性别审美单边主义传统,大胆建构“女人好男色”的性别审美新思维、新逻辑,并将“好色”上升到“审美”的高度予以性别认同,如新锐、前卫女作家万芳在其争议性作品《我是谁的谁是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一段描写就极具代表性:“我觉得我更喜欢也更适合和各种各样的男人交往。可能是基于我以上这些自以为是的思想和论调,周围的朋友们便送了我一顶硕大无比的帽子——‘好色’。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好色就好色吧。其实这个世界的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人好名,有人好利,有人好富,有人好贵,当然也有人好色。‘好色’这个词的意义因个人理解的不同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不一定都代表堕落与淫癖邪恶,起码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对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产生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赞美与渴望。”很明显,与传统男权文化将“色”界定为既“淫”且“秽”的“色情”根本不同,当代都市女作家笔下的“色”无疑已具备了崭新的性别审美内涵,而这种性别审美内涵的核心,,理应是男女两性之间自然美好、风情万种且又互为吸引、充满魔力的情感和欲望。尤为重要的是,在男女两性这种前所未有的情感、欲望关系中,女性已破天荒地由欲望对象蜕变为欲望主体,或曰欲望审美的主体;而女性欲望主体身份的确立,则代表着一种新的性文化观念的正在生成。这种新的性文化观念之于女性解放的意义,正如性别文化研究专家孙绍先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在新的性文化观念中,女性也是正常性爱的发出者,性爱于女性不仅仅是接受,更重要的是主体的一种选择。因此,女性不仅是‘美’的奉献者,也应当是‘美’的选择者。这意味着长期逃出女性审美视野的‘男性美’也应当向女性的选择目标复归。……无论从男女两性的生命关系,还是文化关联来说,女性都当然拥有欣赏男性美、选择男性美的权力。这种出自女性主体的意志和行为,当是女子性爱的基本出发点,是女性彻底摆脱物体境地的根本出路。”
其次,情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多元,是当代都市新潮女性经由情爱革命走向自我解放的必然选择。历史地看,女性为争取情爱自由和自主,曾经走过漫长、曲折的抗争之路。早在20世纪初叶,一些深受女权思潮影响和启发进而觉醒的先进女性,就已开始为自己的情爱自由发出激愤的抗议之声,如女诗人黄婉发表于1919年《新诗年选》上的白话诗作《自觉的女子》,就真实、形象地表达了女性的这种爱情抗争:“我没有见过他/怎么能爱他?/我没有爱他,怎么能嫁他?/……这简直是一件买卖/拿人当牛马罢了/我要保全我的人格/还怎么能承认什么礼教呢/爸爸,你一定要强迫我/我便只有自杀了。”事实上,这种如同女作家冯沅君在其著名小说《隔绝》、《隔绝之后》中借女主人公隽华之口所喊出的“不得自由毋宁死”的誓死抗议,已成为那个社会女性反抗人身禁锢、追求情爱自主的时代强音。作为那一时代强音的历史回响,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却是新时代女性更加从容、自信且毋庸置疑的爱情宣告——“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深圳女作家缪永在其著名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中所发出的这一句充满挑战且无所畏惧的爱情宣告,实际上代表了当代都市新潮女性追求自由、自主情爱生活的普遍心态和心声。毫无疑问,自由的情爱生活追求必然产生多元的情爱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情爱价值取向。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强大的思想解放时代潮流的推动,这种多元的情爱生活方式从较早的“未婚同居”、“试婚同居”,到其后的“一夜情”、“一夜性”,再到晚近由于互联网发达而盛行起来的“网恋”、“网婚”,明显呈现出与时代和社会发展同步的演进态势。此外,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合同制情人”、“女同性恋”等在内的更鲜为人知的另类情爱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纳入到都市女作家的文学表现视野,其中描写“合同制情人”的作品如缪永的《驶出欲望街》,描写“女同性恋”的作品如格子的《迷情的日子》等,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统而观之,当代都市新潮女性自由多元、丰富多彩的情爱生活方式其价值理念明显溢出了传统情爱伦理和道德的既定框范,而表现出强烈的颠覆性和反叛色彩。从女性解放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颠覆和反叛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对男权传统文化的不断颠覆和反叛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才有望得以确立和提升。
二、婚姻主体:“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
一般而言,情爱观念、情爱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婚姻观念、婚姻生活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因此,伴随当代情爱观念和情爱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型,都市新潮女性其婚姻观念和婚姻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和转型。而促使当代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和转型的最为根本的动因,主要在于都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这种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促使女性彻底抛弃了男尊女卑、人身依附的弱者意识,还极大唤醒了女性自我独立的强者意识。而对女性自我独立的强者意识的表现和张扬,一直以来就是当代都市女性写作非常注重的一个文学主题。
新时期文学之初,女作家张辛欣就在《在同一地平线上》(原载《收获)1981年第6期)这篇后来产生了广泛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为了事业、为了自我人格独立而主动放弃婚姻的女性强者形象。在作品中,开始“我”是把婚姻和爱人看得高于一切,像很多具有潜在“夫贵妻荣”传统思想意识的女性一样,甘愿做出了很多自我牺牲和奉献:“为了给他调来北京,开辟事业上的道路创造条件,我放弃了去年最后一次报考普通大学的机会,结了婚。”然而,经过长时间深刻而痛苦的婚姻反思,“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还能退到哪儿去呢?难道把我的点点追求也放弃?不,等到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当我没有把我的爱好和追求当作锻炼智力的游戏和装饰品,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无法保持我和他之间的平衡,无法维持这个家庭的平衡。我还是什么也得不到……”终于,几番思想斗争和挣扎之后,“我”离了婚,并且经过刻苦努力,如愿以偿考上了自己向往已久的电影学院导演系。正如该作品的标题“在同一地平线上”所明白无误寓示的那样,女主人公“我”对事业的拼力追求,实际上凸显了当代女性强烈的性别平等意识,她们试图通过自己事业和智能的提升,真正实现与男人站在人格和价值的“同一地平线上”,因为“当社会更多地以智能归类,同等智能的男女得以站在同一层面上时,就总体而言,男人也就失去了俯视女人的高度,两性的价值也就开始需要重新界定。”因此,作品里“我”从最初的忽略事业,迷信婚姻和家庭,到后来的视事业追求高于一切,这一巨大转变,真切体现了当代知识女性灵魂深处的性别觉醒尤其主体意识的提升,这种觉醒和提升,不仅强化了女性虚弱已久的人格独立意识,还直接构成了对传统婚姻观念和婚姻模式的最有力、最具反叛色彩的解构和冲击。
从女性命运的历史发展来看,女性的人格独立问题,一直成为事关女性解放的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问题。而某种意义上,女性的人格独立至少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是经济的问题,其二是性的问题。这正如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问论及妇女解放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这里所谓的“经济解放”,是指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实现经济自主和经济独立;而所谓“性的解放”,是指女性彻底打破男权社会长期以来愚弄、禁锢女性的“性神话”,成为两性性别关系尤其欲望关系中的“性主体”和“欲望主体”。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社会,这种明显有悖传统男权意志和世俗观念的对于“经济解放”和“性解放”的大胆追求,早已成为都市新潮女性建构自我主体意识和自我独立人格的重要日常生活内容。在都市女作家所着力塑造的诸多此类新潮女性形象中,张欣小说《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中的商晓燕,无疑是其中最突出、最为典型的一个。作为大都市中既年轻、性感又聪明、智慧的现代职业女性,商晓燕“活得相当自我,自己是自己的圆心和半径”。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活我的,不按照任何人的愿望活。”在她的意识里,什么“贞操节烈”、“从一而终”等腐朽观念早已荡然无存。因此,她虽未婚,却并不放弃对性爱的追求和享受;为了自己情欲的满足和事业的发展,她机智地周旋于自己心仪的两个优秀男人之间,“只睡觉,不结婚”,“对男人的取舍完全看自己的需求”。她坚信:“自己有本事还愁身边没男人吗?”而她充满自我独立意识的婚姻理念尤为深刻和前卫:“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在她看来,爱情对于婚姻固然重要,但自由、独立尤其经济独立对于婚姻更为重要——“靠谁都是靠不住的,我只能靠我自己”。如果从源远流长的婚姻传统看,商晓燕的思想和行为显然已属伤风败俗,大逆不道;但从女性主义的高度看,她的这种思想行为无疑构成了女性解放先锋所应具备的最为可贵的品质和个性。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学作品就已经开始注重真实地再现那个时代新潮女性强烈的婚姻主体意识,典型的如丁玲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原载《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之11、12号)中塑造的玛丽,就是一个敢于冒犯传统、世俗的婚姻观念和婚姻体制,如同商晓燕一样坚执“只恋爱,不结婚”思想的先锋、新潮女性。玛丽似乎早已看穿了传统婚姻“囚禁”女性的本质,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她宁可选择“不婚”:“她知道女人一同人结了婚,一生便算终结了。做一个柔顺的主妇,接着便做一个好母亲,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女,所谓的家庭温柔,便剥蚀去许多其余的幸福,而且一眨眼,头发白了,心也灰了,一任那健壮的丈夫在外面浪游,自己只打叠起婆婆的慈心,平静地等待着做祖母……这有什么意义!她不需要,她很满足她现有的,一种自由的生活。”像玛丽和商晓燕们一样,在当代中国日益开放和进步的广大都市社会,崇尚“只恋爱,不结婚”的另类、自由女性已经越来越多。而促使她们做出“不婚”选择的根本原因,除去为了维护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还在于她们对传统婚姻那种日常化的矛盾、纠葛、冲突甚至暴力的深深恐惧和极度失望,当代新锐女作家小意在其长篇小说《蓝指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中通过女主人公之口所抒发的一段感慨,就极具代表性地表达了她们对传统婚姻的深深困惑、恐惧和失望:“婚姻?婚姻?这就是婚姻?从小听着、看着大人们吵,看着爸爸生气的脸,看着妈妈流泪的眼,看着纷争迭起,纠缠不清,只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又似解不开的疙瘩,一天天,一年年,堆积着相互的不满,凝集着对生活的厌倦。他们都不快乐,但都没有勇气改变了……这样不累吗?这样才能叫婚姻吗?如果人活着如此孤独,那么找人结婚就是要相互取暖,到头来是这样一个结局有什么温暖可言呢?无异于找个人来折磨自己。我不知道别人家庭都是什么样的,我想也差不多,很多同学朋友也会对我说起他们的家庭,几乎大同小异。我真是不明白,这样麻木的痛苦都是人们自愿找来的,人真的是很闲,闲着没事给自己找麻烦。一个人的时候怕孤独,两个人又怕辜负,没辜负的时候还是不舒服。人,永远不会满足,所以永远痛苦。”其实传统婚姻存在的弊害远不止夫妻怄气和吵架,它常常还会遭遇婚外情、家庭暴力、夫妻反目甚至离婚等更为严峻的人生问题。因此,为避免婚姻有可能带来的痛苦、折磨和伤害,觉醒而自立的都市女性纷纷远离婚姻,甚至回避所谓爱情,诸如赵凝的《有毒的婚姻》(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王心丽的《单身逃亡》(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夏可可的《一个人的爱情》(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林哲的《不相信爱情》(花艺出版社1996年版),于艾香的《有爱即有忧》(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盛可以的《无爱一身轻》(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赵赵的《动什么,别动感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都是对当代女性这种逃避婚姻甚至回避感情等社会性别现象进行深入描写的代表性作品。当代女性的这种极具反叛色彩的婚姻观念及其生活方式的选择,显然是对传统婚姻体制进行深刻的怀疑、反思和批判的结果。这种怀疑、反思和批判,彰显了都市新潮女性强烈的婚姻主体意识,即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她们已不再是被动地去迎合与屈就,而是主动地去自我把握和选择符合自己意志和意愿的情感生活方式。
总之,对于女权意识逐渐觉醒的中国当代都市女性而言,其身体主体意识以及情爱主体意识和婚姻主体意识的凸显和张扬,在性别解放的意义上,“意味着重新确立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意志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物质精神存在与女性符号称谓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关系、女性的称谓与男性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是我自己的’这短短六个字竟是女性向整个语言符号系统的挑战……这一瞬间结束了女性的绵延两千年的物化、客体的历史,开始了女性们主体生成阶段。”而女性由“对象”到“主体”的这种革命性转变和历史性跨越,确定无疑地昭示了一种性别平等意义上的两性关系正在日渐生成,并必将成为性别文化革命最基本的内容和最主要的动力。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5389037508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
网址: 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
作为一种特别关注当代都市社会中各种复杂性别问题和性别现象的“性别”文学,中国当代的都市女性写作因其突出的性别视角和明显的反男权叙事,而成为一种具有鲜明女性主义思想、艺术新质的复杂文学现象。与充满男权意识的传统、正统文学或主流文学的价值取向大异其趣,都市女性写作有着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整体上看,都市女性写作的价值追求最主要体现在对女性性别主体意识的积极建构上,女性的性别主体意识无疑已构成了都市女性写作的价值体系中最为核心,、最为重要的部分。所谓“性别主体意识”,是指在都市女作家笔下的各种性别关系中,女性已不再甘心于男权社会及其性别文化传统强行派定的“次性”、“他者”、“第二性”等屈辱的性别身份,而是力图通过性别抗争和性别革命恢复与男性同等的主体性地位和人格尊严。都市女性写作的这种性别主体意识,主要体现在其所塑造的当代新潮女性与传统女性判然有别,与传统观念格格不人的情爱主体意识以及婚姻意识等诸多层面,凸显了充分浸淫现代女权思想的一代新女性具有性别革命意义的精神觉醒和思想成长。
一、情爱主体:“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情爱”,是人类两性最基本的性别关系之一,它构成了人类两性最基本的日常生活内容,它尤其是青年男女温馨浪漫、最富生命激情的精神生活内容。然而,在充满性别歧视的男权文化传统及其性别体制的强力约束之下,女性“爱”的资格、权力和机会几乎被剥夺殆尽。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也很难说女性已经完全享有了性别平等意义上的“爱”的权力。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都市女作家笔下的那些新潮女性其前卫的情爱观念以及对情爱的大胆追求和与传统相悖的另类情爱生活方式,才充分显现出颇具反叛色彩的性别觉醒和情爱革命的尖锐锋芒。
首先,情爱观念的根本转变,成为当代新潮女性性别觉醒和情爱革命最为重要的关键步骤。在当代都市女作家所塑造的诸多新潮女性人物群像中,这种情爱观念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这些新潮女性一改传统女性对待情爱的被动心态,大胆、主动地追求心中的理想爱情,有的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典型的如王安忆在其著名的“三恋”之一的《荒山之恋》(原载《十月》1986年第4期)中塑造的金谷巷女孩。作为有夫之妇,金谷巷女孩不顾世俗流言,疯狂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但最后二人终究难敌来自世俗社会方方面面的强大压力,双双殉情。作为这一爱情悲剧的主角,金谷巷女孩最令人喟叹、感佩的,也许并不是她的最后殉情,而是她积极主动、不顾一切地追求爱情的叛逆性格和执着精神。其二是这些新潮女性一改传统女性的从属、依附心理,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情爱自主、情爱平等意识,这正如当代著名女诗人舒婷在其名作《致橡树》中所宣告的那样:“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女性在两性情爱生活中的这种凸显的自主、平等意识,无疑表征着女性人格意识、尊严意识也即性别主体意识的高度觉醒。其三是新潮女性勇于改写“男人好女色”的性别审美单边主义传统,大胆建构“女人好男色”的性别审美新思维、新逻辑,并将“好色”上升到“审美”的高度予以性别认同,如新锐、前卫女作家万芳在其争议性作品《我是谁的谁是谁》(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中的一段描写就极具代表性:“我觉得我更喜欢也更适合和各种各样的男人交往。可能是基于我以上这些自以为是的思想和论调,周围的朋友们便送了我一顶硕大无比的帽子——‘好色’。我对此很不以为然,好色就好色吧。其实这个世界的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有人好名,有人好利,有人好富,有人好贵,当然也有人好色。‘好色’这个词的意义因个人理解的不同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不一定都代表堕落与淫癖邪恶,起码对我来说,它是一种对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所产生的那种发自内心的赞美与渴望。”很明显,与传统男权文化将“色”界定为既“淫”且“秽”的“色情”根本不同,当代都市女作家笔下的“色”无疑已具备了崭新的性别审美内涵,而这种性别审美内涵的核心,,理应是男女两性之间自然美好、风情万种且又互为吸引、充满魔力的情感和欲望。尤为重要的是,在男女两性这种前所未有的情感、欲望关系中,女性已破天荒地由欲望对象蜕变为欲望主体,或曰欲望审美的主体;而女性欲望主体身份的确立,则代表着一种新的性文化观念的正在生成。这种新的性文化观念之于女性解放的意义,正如性别文化研究专家孙绍先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在新的性文化观念中,女性也是正常性爱的发出者,性爱于女性不仅仅是接受,更重要的是主体的一种选择。因此,女性不仅是‘美’的奉献者,也应当是‘美’的选择者。这意味着长期逃出女性审美视野的‘男性美’也应当向女性的选择目标复归。……无论从男女两性的生命关系,还是文化关联来说,女性都当然拥有欣赏男性美、选择男性美的权力。这种出自女性主体的意志和行为,当是女子性爱的基本出发点,是女性彻底摆脱物体境地的根本出路。”
其次,情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多元,是当代都市新潮女性经由情爱革命走向自我解放的必然选择。历史地看,女性为争取情爱自由和自主,曾经走过漫长、曲折的抗争之路。早在20世纪初叶,一些深受女权思潮影响和启发进而觉醒的先进女性,就已开始为自己的情爱自由发出激愤的抗议之声,如女诗人黄婉发表于1919年《新诗年选》上的白话诗作《自觉的女子》,就真实、形象地表达了女性的这种爱情抗争:“我没有见过他/怎么能爱他?/我没有爱他,怎么能嫁他?/……这简直是一件买卖/拿人当牛马罢了/我要保全我的人格/还怎么能承认什么礼教呢/爸爸,你一定要强迫我/我便只有自杀了。”事实上,这种如同女作家冯沅君在其著名小说《隔绝》、《隔绝之后》中借女主人公隽华之口所喊出的“不得自由毋宁死”的誓死抗议,已成为那个社会女性反抗人身禁锢、追求情爱自主的时代强音。作为那一时代强音的历史回响,在今天,我们听到的却是新时代女性更加从容、自信且毋庸置疑的爱情宣告——“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深圳女作家缪永在其著名小说《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中所发出的这一句充满挑战且无所畏惧的爱情宣告,实际上代表了当代都市新潮女性追求自由、自主情爱生活的普遍心态和心声。毫无疑问,自由的情爱生活追求必然产生多元的情爱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情爱价值取向。自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强大的思想解放时代潮流的推动,这种多元的情爱生活方式从较早的“未婚同居”、“试婚同居”,到其后的“一夜情”、“一夜性”,再到晚近由于互联网发达而盛行起来的“网恋”、“网婚”,明显呈现出与时代和社会发展同步的演进态势。此外,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合同制情人”、“女同性恋”等在内的更鲜为人知的另类情爱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纳入到都市女作家的文学表现视野,其中描写“合同制情人”的作品如缪永的《驶出欲望街》,描写“女同性恋”的作品如格子的《迷情的日子》等,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统而观之,当代都市新潮女性自由多元、丰富多彩的情爱生活方式其价值理念明显溢出了传统情爱伦理和道德的既定框范,而表现出强烈的颠覆性和反叛色彩。从女性解放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颠覆和反叛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只有在这种对男权传统文化的不断颠覆和反叛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才有望得以确立和提升。
二、婚姻主体:“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
一般而言,情爱观念、情爱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婚姻观念、婚姻生活方式的发展和变化;因此,伴随当代情爱观念和情爱生活方式的急剧转型,都市新潮女性其婚姻观念和婚姻生活方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和转型。而促使当代婚姻观念发生变化和转型的最为根本的动因,主要在于都市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这种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不仅促使女性彻底抛弃了男尊女卑、人身依附的弱者意识,还极大唤醒了女性自我独立的强者意识。而对女性自我独立的强者意识的表现和张扬,一直以来就是当代都市女性写作非常注重的一个文学主题。
新时期文学之初,女作家张辛欣就在《在同一地平线上》(原载《收获)1981年第6期)这篇后来产生了广泛文学影响和社会影响的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为了事业、为了自我人格独立而主动放弃婚姻的女性强者形象。在作品中,开始“我”是把婚姻和爱人看得高于一切,像很多具有潜在“夫贵妻荣”传统思想意识的女性一样,甘愿做出了很多自我牺牲和奉献:“为了给他调来北京,开辟事业上的道路创造条件,我放弃了去年最后一次报考普通大学的机会,结了婚。”然而,经过长时间深刻而痛苦的婚姻反思,“我”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还能退到哪儿去呢?难道把我的点点追求也放弃?不,等到我自己什么也没有了,无法和他在事业上、精神上对话,我仍然会失去他!当我没有把我的爱好和追求当作锻炼智力的游戏和装饰品,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无法保持我和他之间的平衡,无法维持这个家庭的平衡。我还是什么也得不到……”终于,几番思想斗争和挣扎之后,“我”离了婚,并且经过刻苦努力,如愿以偿考上了自己向往已久的电影学院导演系。正如该作品的标题“在同一地平线上”所明白无误寓示的那样,女主人公“我”对事业的拼力追求,实际上凸显了当代女性强烈的性别平等意识,她们试图通过自己事业和智能的提升,真正实现与男人站在人格和价值的“同一地平线上”,因为“当社会更多地以智能归类,同等智能的男女得以站在同一层面上时,就总体而言,男人也就失去了俯视女人的高度,两性的价值也就开始需要重新界定。”因此,作品里“我”从最初的忽略事业,迷信婚姻和家庭,到后来的视事业追求高于一切,这一巨大转变,真切体现了当代知识女性灵魂深处的性别觉醒尤其主体意识的提升,这种觉醒和提升,不仅强化了女性虚弱已久的人格独立意识,还直接构成了对传统婚姻观念和婚姻模式的最有力、最具反叛色彩的解构和冲击。
从女性命运的历史发展来看,女性的人格独立问题,一直成为事关女性解放的最为根本、最为关键的问题。而某种意义上,女性的人格独立至少涉及两个基本的问题,其一是经济的问题,其二是性的问题。这正如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问论及妇女解放问题时所强调的那样:“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这里所谓的“经济解放”,是指女性摆脱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实现经济自主和经济独立;而所谓“性的解放”,是指女性彻底打破男权社会长期以来愚弄、禁锢女性的“性神话”,成为两性性别关系尤其欲望关系中的“性主体”和“欲望主体”。在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日新月异的当代中国社会,这种明显有悖传统男权意志和世俗观念的对于“经济解放”和“性解放”的大胆追求,早已成为都市新潮女性建构自我主体意识和自我独立人格的重要日常生活内容。在都市女作家所着力塑造的诸多此类新潮女性形象中,张欣小说《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中的商晓燕,无疑是其中最突出、最为典型的一个。作为大都市中既年轻、性感又聪明、智慧的现代职业女性,商晓燕“活得相当自我,自己是自己的圆心和半径”。她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活我的,不按照任何人的愿望活。”在她的意识里,什么“贞操节烈”、“从一而终”等腐朽观念早已荡然无存。因此,她虽未婚,却并不放弃对性爱的追求和享受;为了自己情欲的满足和事业的发展,她机智地周旋于自己心仪的两个优秀男人之间,“只睡觉,不结婚”,“对男人的取舍完全看自己的需求”。她坚信:“自己有本事还愁身边没男人吗?”而她充满自我独立意识的婚姻理念尤为深刻和前卫:“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在她看来,爱情对于婚姻固然重要,但自由、独立尤其经济独立对于婚姻更为重要——“靠谁都是靠不住的,我只能靠我自己”。如果从源远流长的婚姻传统看,商晓燕的思想和行为显然已属伤风败俗,大逆不道;但从女性主义的高度看,她的这种思想行为无疑构成了女性解放先锋所应具备的最为可贵的品质和个性。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文学作品就已经开始注重真实地再现那个时代新潮女性强烈的婚姻主体意识,典型的如丁玲在《一九三○年春上海之二》(原载《小说月报》1930年第21卷之11、12号)中塑造的玛丽,就是一个敢于冒犯传统、世俗的婚姻观念和婚姻体制,如同商晓燕一样坚执“只恋爱,不结婚”思想的先锋、新潮女性。玛丽似乎早已看穿了传统婚姻“囚禁”女性的本质,因此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她宁可选择“不婚”:“她知道女人一同人结了婚,一生便算终结了。做一个柔顺的主妇,接着便做一个好母亲,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女,所谓的家庭温柔,便剥蚀去许多其余的幸福,而且一眨眼,头发白了,心也灰了,一任那健壮的丈夫在外面浪游,自己只打叠起婆婆的慈心,平静地等待着做祖母……这有什么意义!她不需要,她很满足她现有的,一种自由的生活。”像玛丽和商晓燕们一样,在当代中国日益开放和进步的广大都市社会,崇尚“只恋爱,不结婚”的另类、自由女性已经越来越多。而促使她们做出“不婚”选择的根本原因,除去为了维护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还在于她们对传统婚姻那种日常化的矛盾、纠葛、冲突甚至暴力的深深恐惧和极度失望,当代新锐女作家小意在其长篇小说《蓝指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中通过女主人公之口所抒发的一段感慨,就极具代表性地表达了她们对传统婚姻的深深困惑、恐惧和失望:“婚姻?婚姻?这就是婚姻?从小听着、看着大人们吵,看着爸爸生气的脸,看着妈妈流泪的眼,看着纷争迭起,纠缠不清,只是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又似解不开的疙瘩,一天天,一年年,堆积着相互的不满,凝集着对生活的厌倦。他们都不快乐,但都没有勇气改变了……这样不累吗?这样才能叫婚姻吗?如果人活着如此孤独,那么找人结婚就是要相互取暖,到头来是这样一个结局有什么温暖可言呢?无异于找个人来折磨自己。我不知道别人家庭都是什么样的,我想也差不多,很多同学朋友也会对我说起他们的家庭,几乎大同小异。我真是不明白,这样麻木的痛苦都是人们自愿找来的,人真的是很闲,闲着没事给自己找麻烦。一个人的时候怕孤独,两个人又怕辜负,没辜负的时候还是不舒服。人,永远不会满足,所以永远痛苦。”其实传统婚姻存在的弊害远不止夫妻怄气和吵架,它常常还会遭遇婚外情、家庭暴力、夫妻反目甚至离婚等更为严峻的人生问题。因此,为避免婚姻有可能带来的痛苦、折磨和伤害,觉醒而自立的都市女性纷纷远离婚姻,甚至回避所谓爱情,诸如赵凝的《有毒的婚姻》(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王心丽的《单身逃亡》(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夏可可的《一个人的爱情》(海天出版社2006年版),林哲的《不相信爱情》(花艺出版社1996年版),于艾香的《有爱即有忧》(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盛可以的《无爱一身轻》(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赵赵的《动什么,别动感情》(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都是对当代女性这种逃避婚姻甚至回避感情等社会性别现象进行深入描写的代表性作品。当代女性的这种极具反叛色彩的婚姻观念及其生活方式的选择,显然是对传统婚姻体制进行深刻的怀疑、反思和批判的结果。这种怀疑、反思和批判,彰显了都市新潮女性强烈的婚姻主体意识,即在婚姻和爱情问题上,她们已不再是被动地去迎合与屈就,而是主动地去自我把握和选择符合自己意志和意愿的情感生活方式。
总之,对于女权意识逐渐觉醒的中国当代都市女性而言,其身体主体意识以及情爱主体意识和婚姻主体意识的凸显和张扬,在性别解放的意义上,“意味着重新确立女性的身体与女性的意志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物质精神存在与女性符号称谓的关系,重新确立女性的存在与男性的关系、女性的称谓与男性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是我自己的’这短短六个字竟是女性向整个语言符号系统的挑战……这一瞬间结束了女性的绵延两千年的物化、客体的历史,开始了女性们主体生成阶段。”而女性由“对象”到“主体”的这种革命性转变和历史性跨越,确定无疑地昭示了一种性别平等意义上的两性关系正在日渐生成,并必将成为性别文化革命最基本的内容和最主要的动力。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5389037508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
网址: 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