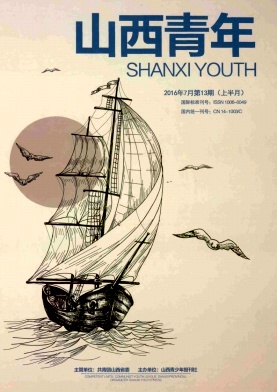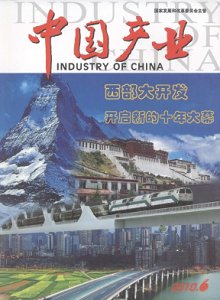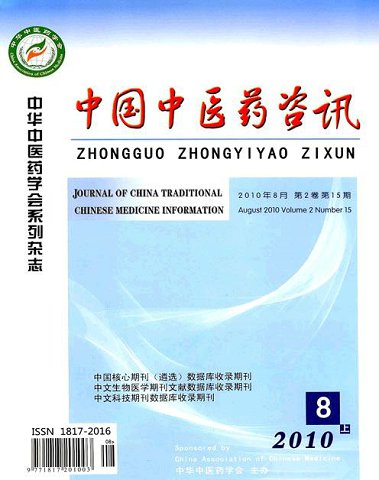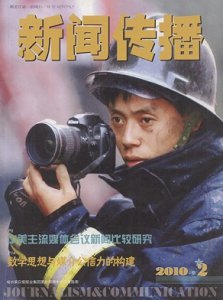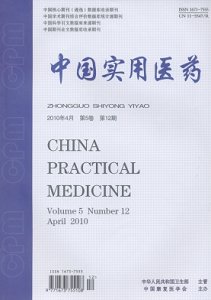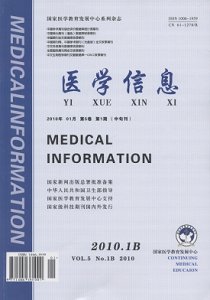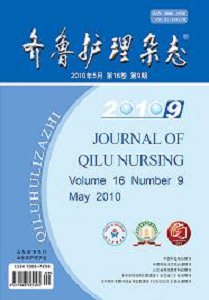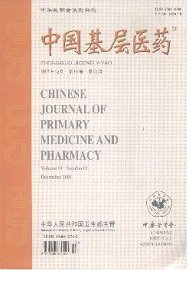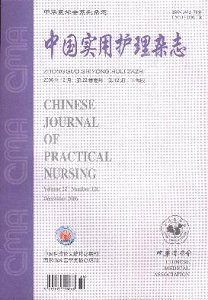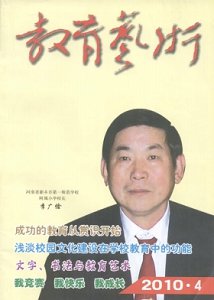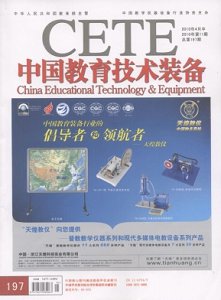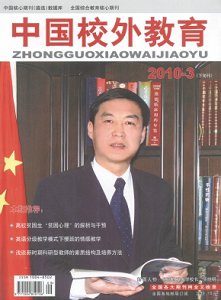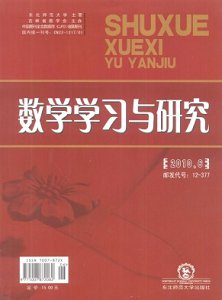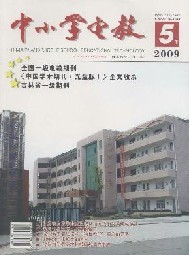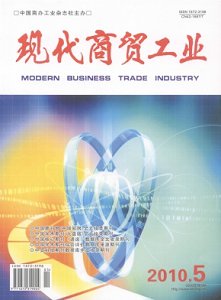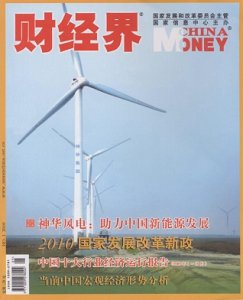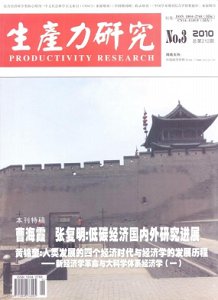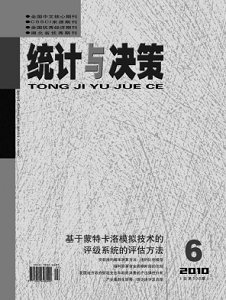谈我国的汉字简化问题
一
语言是人类的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语言的工具。人类对于任何一种工具,都要求它具有高效率的特点。所谓高效率,一般说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速度快,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多而且做得好;二是成本低,消耗少,省力气、省时间,自然也会省财物。理想的工具,人们要求它能达到“多快好省”。人们对于文字同样有这样的要求。我们既要文字简,结构简单,笔画少,写起来快而省力;又要文字明,能很好地表达语言,字与字之间分辨率高,不会表意混淆,妨碍交际。正是两方面的要求,就造成了汉字四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不断简化和繁化的现象。简化,要文字简易,好学、好写、好记;繁化要文字明确,分辨率强,好认、好用。
由于汉字历史悠久,使用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用它记载的典籍数量多、时间跨度大,再加上刊刻、排校方面的原因,使得汉字发展到现代显得十分庞杂:总的字数太多,异体字太多,一些字笔画太多,使人感到难学、难认、难写、难用。上世纪前半期,不少仁人志士,认为是汉字拖累了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拖累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至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强盛。他们立志要对汉字进行革命,搞汉字改革,搞拼音文字。这些前辈们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爱国者,是革命者。但是,他们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19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我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掠夺,三座大山压得广大民众喘不过气来。国力积弱,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事业难以发展。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苟延性命尚不能够,遑论去识字学习,提高科学技术?直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的文盲数量惊人,以至于有些人还为自己是大老粗、工农干部为荣呢。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进行政治革命,强化经济基础,才是发展文化教育,发展科技,解决识字用字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不考虑政治、经济的根本问题,只是责怪文字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只能是本末倒置。当然,无庸讳言,文字作为一种辅助语言的重要工具,有优劣之分、难易之别,有整理、改进甚至改革的问题。文字对文化教育、科技进步以至于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或改革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汉字的繁难问题确实是突出的,字数多、异体多、笔画多,结构复杂,易生讹变。这给对汉字的学习、书写、使用以及汉字机械化、信息化都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自然,汉字的这些问题不是现代才有,而是在它的发展史上伴随其不断的演变、改进而陆续产生的。我国历代政府也对汉字做过一些整理、统一工作。但简化工作的推动力量还是民间的自发运用和约定俗成。比较起来,新中国建国后进行的汉字整理和简化工作规模之大、力度之强、成效之显著都是以前的任何一次不可比拟的。1952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重点研究汉字简化问题。1953年毛泽东主席指出:“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1955年1月文改会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为慎重起见,方案中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从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先后分四批推行。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经过补充、调整,简化字由方案收录的515个增加到2236个,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又对原来总表中的个别字进行了调整。
二
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汉字简化的方针规定为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约定俗成,就是广大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或认定的使用简体字的习惯。现在看来,这条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汉字简化方案》和总表中的简化字,绝大多数是有约定俗成的基础的,有其稳定性和普遍性。汉字简化使数量可观的常用汉字笔画得到简化,也减少了一定数量的汉字。这次简化基本上是成功的,是受我国大陆的广大群众欢迎的。但是,由于当时推行简化汉字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只是把汉字简化工作当作改革汉字、通向拼音文字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吴玉章),变成一种短期的行为,对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好像能较快地实现汉字的拼音化,所以对整理和简化汉字的理论和方法、汉字的学理和系统性、古今贯通、繁简转换、海内外协调、字形的匀称美观等问题缺乏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所说汉字简化应包括形体和数量两个方面的简化,是很正确的。但也必须看到简化中会产生字形简与明的矛盾,字量过少与对语言的精确表达的矛盾以及某些简化造成自乱系统的问题。求稳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分批推行,隔一两年推行一批,会使文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处在不停变动的状态之中,原有系统破坏了,相对稳定的新系统又形成不起来,这不能不给文字的发展和运用带来消极的影响。1977年12月《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及推行没过多久,即被通知停止使用以至被废止,正是其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所造成的。
我们认为,要确定简化字,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条原则:
一、约定俗成。也就是说要确定的简化字在汉字运用的实践中有普遍性和稳定性,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简化字绝大多数都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很多是民间长期流行的俗字、简体字,所以较容易在群众中推行。而“二简”中的一些字有的只在个别行业或某个地区使用,普遍性不强。有的为简而简,是少数人新造的,缺乏约定俗成的基础,所以难以在社会上推行。
二、效率原则。前面说过文字作为一种重要工具,人们会从运用它进行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要求它。选定简化字同样有这种要求,既要求所确定的简化字字形是简易的,笔画少,学和写快而省力;同时又要求跟其他字的区别性强,对语言的表达是明确的,认字和用字确切、方便。
三、规律性。毛泽东主席对汉字简化的指示,强调“找出简化规律”,“有规律地进行简化”,这是很重要的。汉字的产生、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创造、变化一般说来有一定的理据,发展演变有一定的系统性。当然,理据、系统是相对的,汉字的系统性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是动态的。经过简化的汉字系统与原来的繁体字系统就有变化。要求文字的发展变化一点也不去变动旧有系统是不正确的,比如,我们不能以《说文解字》系统约束后来的汉字演变,也不能以繁体字系统限制汉字简化。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汉字系统在发展中有传承性,如在原有系统不被打破或较少破坏的条件下一样可以发展到新的系统,还是多一些继承原系统为好。文字的稳定性强,传承性高,有利于文字的运用和对以前文献及传统文化的继承。
三
文改会通过制定汉字简化方案,总结了创造简化字的方法和经验,将简化字划分为八种类型:1、假借字。借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较繁的同音字或异音字,比如脸面的“面”代替面粉的“麵”、山谷的“谷”代替谷子的“榖”,是同音假借;占卜的“卜”代替萝卜的“蔔”、升斗的“斗”代替斗争的“鬥”,是异音假借。2、形声字。指用形声结构造字原理简化汉字,这又有几种情况。A、原字的笔画太繁的形符改为笔画较简的,如刮风的刮-颳、肮脏的肮-骯。B、原字的笔画太繁的声符改为笔画较简的,如袄-襖、衬-襯、础-礎;也有原字的笔画较繁的形符和声符同时都改为笔画较简的,如脏-髒、惊-驚。C、原字的笔画较繁的非形声字改为笔画较简的新形声字,如邮-郵、窜-竄。3、草书楷化字。指将繁体字的行书、草书写法,改为楷书的形式,如东(東)、车(車)、贝(貝)。4、特征字。指用原字的特征部分来代替原字,有的留一角,如声(聲)、医(醫);有的留一半,如录(錄)、号(號)、丽(麗);有的留大部分,如垦(墾)、阳(陽)、际(際)。5、轮廓字。指保留原字的轮廓,省略其中的部分笔画,如卤(鹵)、乌(烏)。6、会意字。指用几个笔画少的意义相关的字或偏旁表示一个意义,构成一个字。如尘(塵)、笔(筆)、泪(淚)。7、符号字。指把原字中笔画繁难的部分,用简单的字与笔画代替,这些字和笔画在字中不表音或义,只起符号的作用。如用“又”的汉、叹、艰、难、欢、观、权、劝、仅、鸡、戏、邓、对,用“不”的还、环、坏、怀。8、偏旁类推字。指运用已简化的字或偏旁类推出来的字。如军(軍)、阵(陣)、连(連)、诨(諢)。
在简化字的八种类型中,草书楷化字,一般为独体字,因为是汉字原有的一种字,这种字可明显地减少字的笔画,又不会增加汉字字数,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但是这种情况在简化字中所占比例很小。特征字、轮廓字、会意字、符号字之类,如果是约定俗成的早已流行的字,既可以减少字的笔画,又不会增加汉字字数,也是不错的办法。但是这几种办法中都还有一些新造的简体字,比如“导、卫、邓、击、严、农、乡、盘”等,作为单字是简化了,作为汉字字数并没有减少,有的打破原有系统性,对学、认有关的字却未必有利。如“盘”,把上半的“般”换作“舟”,少了四画,但汉字中又多了个“盘”字,而且与“般、搬、瘢、磐”失去了系统;“导”字与“道”没有了关系;“邓”与“登、蹬、瞪、簦、凳、磴、镫、澄”系统脱了钩。
下面我们想着重谈谈简化字中形声字和偏旁类推字以及假借字问题。如前所说,简化字中的形声字,是以形声结构的原理进行简化的字。形声字有表音和表意的偏旁,在汉字系统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原有形声字基础上简化偏旁的简化字,既维持了原来的形声结构,又在字形上与原字有较多联系,便于学习和辨认,这种办法比较受欢迎,也是文改主管部门较为注重的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中无论是代替原来的非形声字而新造出来的形声字还是将原来形声字的形符、声符进行改换形成新的形声字,都是减少了一个繁体字,增加了一个简化字,只是减少了字的笔画,没有减少字数。这与前面说到的几种办法的缺欠是相同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偏旁类推字,是运用简化的偏旁或字作为偏旁和部件类推出来的简化字。这种办法简化效率很高,《简化字总表》的第三表就是运用《汉字简化方案》收入的54个简化偏旁和补充规定的9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类推出来了1754个简化字。由于运用了类推简化办法,使得常用汉字中的相当数量的汉字得到简化,也使汉字经过简化整理形成了与原系统有所不同的新的系统。简化字中的偏旁类推字,与前面说的几种办法存在的问题一样,也是只能减少字的笔画,不能减少字数。废除一个繁体字,增加一个简化偏旁类推的字,字数没有减少,在我们的字典里,只要是繁简都收,就得都收下来,比原先没有简化时多收了一些简化字。新造简化字和类推简化字又为我们的汉字总字库增添出来数量可观的新的成员,这与汉字简化的减少汉字总字数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类推简化还有个范围问题。1964年《简化字总表》的“说明”中指出:“第三表所收的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汉字总数很多,这个表不必尽列。……现在为了适应一般的需要,第三表所列的简化字的范围,基本上以《新华字典》(1962年第三版,只收汉字八千个左右)为标准。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十分清楚,当时的汉字简化工作的主管部门主张类推简化是没有范围限制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所收汉字都是进行类推简化的,198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版本又增收了不少汉字,也是同样类推简化的。这些字典、词典收字不过是一万多,多的也不超过两万。八十年代后,我国要编辑出版大型字典、词典,类推简化就突出了。1986年10月,《汉语大字典》开始出版,在其《凡例》中说:“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发的《简化字总表》所列字目为准。”1986年11月开始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也在《凡例》中说:“简化字只立单字条目”,“夹注及立目的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1964年联合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列的2236个字为限。”也就是说,这两部收字较多的大型辞书(其中《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四千多个),类推简化只限于“总表”范围,以外的不类推简化。但是1994年9月出版的《中华字海》收字85568个,它收字比“大字典”多出三万多,主要是收录了《简化字总表》范围之外的类推简化字,甚至连一些古代的讹字也进行了类推简化。对这两种收录简化字的范围,辞书界也多所议论。近年大型计算机字库的建立,一些古籍的简体字版出版,类推简化的范围问题就更为突出了。我们认为,类推简化不必只限定在“总表”之内,范围可以适当地扩大一些,但也不要毫无限制。是不是可将古今的主要典籍用字弄清楚,把现代地名用字弄清楚,确定个范围。这以外的较为罕见的字,有的只是较专门的古书用到,或者只是古代字书上收录,而古籍上见不到的字,还有的字在字书上也注不出音义的,有的甚至是讹字。一些古代不用现代也不用的字根本不必列入范围,自然更不必类推简化了。也有可能以后还有重要文献出土,需要出简体字本,会有所定范围以外的字,那会是极为有限的,类推简化的范围也可稍作调整的。
假借字问题。用一个笔画简的字替代音同或音近的笔画较繁的字,实际上不仅是替代,而且是兼并。同音代替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就是汉字简化的重要方式。这种办法不仅简化了笔画,而且又减少了字数,这是最为符合汉字简化的目标的,所以它也最受原推行汉字简化的主管部门重视,列为汉字简化的第一种方法,首选的办法。但在文字运用中,这种办法出现的问题较为突出。由于是同音代替,有的还不完全同音,这就给选用的字增加了义,有的还增加了音,就有引起混淆的可能。比如“干”字,近年常见“干细胞”一词,其中的“干”有人读阴平,有人读去声,如不了解术语含义,就难以确定;翻译地名“塔什干”中的“干”,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不止一个人读成去声。再比如,我见到有位经理的名片,全用繁体字,上面的地址“海淀区芙蓉里”中的“淀”印作“澱”,“里”印作“裡”;还有的把“家”字无限制地转换繁体为“傢”字;我买到一本开本很小印装精致《论语》,用繁体字排版,里面当作说话义的“云”,没有例外地全都上面加个“雨”字头印作“雲”;近年出现的“二恶英”一词,因为“恶”是多音字,常用音义是负面的,所以专家们坚持用带“口”旁的“噁”字,简化字表却是把这个字作为“恶”的繁体废除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用同音代替或假借法进行简化而字表又没有注释明白造成的。
由于汉字简化已经推行了四十多年,同音代替又是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它所确定的简化字基本上稳定下来。我们不可能再去改变很多已经形成的这种由假借关系而形成的简化字,只能到底对个别的同音代替容易产生混淆的繁简关系进行适当调整(如“后(後)、发(髮)、谷(穀)、当(噹)、蒙(濛懞矇)”等),对那些原本通用范围受限制的假借加以说明,以防转换时产生错误(如“干(乾亁幹)、斗(鬥)、淀(澱)、范(範)、里(裡裏)”等)。
语言是人类的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语言的工具。人类对于任何一种工具,都要求它具有高效率的特点。所谓高效率,一般说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速度快,在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多而且做得好;二是成本低,消耗少,省力气、省时间,自然也会省财物。理想的工具,人们要求它能达到“多快好省”。人们对于文字同样有这样的要求。我们既要文字简,结构简单,笔画少,写起来快而省力;又要文字明,能很好地表达语言,字与字之间分辨率高,不会表意混淆,妨碍交际。正是两方面的要求,就造成了汉字四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上的不断简化和繁化的现象。简化,要文字简易,好学、好写、好记;繁化要文字明确,分辨率强,好认、好用。
由于汉字历史悠久,使用的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用它记载的典籍数量多、时间跨度大,再加上刊刻、排校方面的原因,使得汉字发展到现代显得十分庞杂:总的字数太多,异体字太多,一些字笔画太多,使人感到难学、难认、难写、难用。上世纪前半期,不少仁人志士,认为是汉字拖累了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拖累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至影响了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强盛。他们立志要对汉字进行革命,搞汉字改革,搞拼音文字。这些前辈们的动机是毋庸置疑的,他们是爱国者,是革命者。但是,他们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19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我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和掠夺,三座大山压得广大民众喘不过气来。国力积弱,经济落后,文化教育事业难以发展。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苟延性命尚不能够,遑论去识字学习,提高科学技术?直到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的文盲数量惊人,以至于有些人还为自己是大老粗、工农干部为荣呢。这就说明了一个道理,进行政治革命,强化经济基础,才是发展文化教育,发展科技,解决识字用字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不考虑政治、经济的根本问题,只是责怪文字阻碍了社会的前进,只能是本末倒置。当然,无庸讳言,文字作为一种辅助语言的重要工具,有优劣之分、难易之别,有整理、改进甚至改革的问题。文字对文化教育、科技进步以至于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这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革命或改革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汉字的繁难问题确实是突出的,字数多、异体多、笔画多,结构复杂,易生讹变。这给对汉字的学习、书写、使用以及汉字机械化、信息化都会带来一些不良影响。自然,汉字的这些问题不是现代才有,而是在它的发展史上伴随其不断的演变、改进而陆续产生的。我国历代政府也对汉字做过一些整理、统一工作。但简化工作的推动力量还是民间的自发运用和约定俗成。比较起来,新中国建国后进行的汉字整理和简化工作规模之大、力度之强、成效之显著都是以前的任何一次不可比拟的。1952年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重点研究汉字简化问题。1953年毛泽东主席指出:“作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出基本形体,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1954年12月,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直属于国务院。1955年1月文改会拟定了《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由国务院正式公布。为慎重起见,方案中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从1956年2月至1959年7月先后分四批推行。1964年5月文改会编印出《简化字总表》。经过补充、调整,简化字由方案收录的515个增加到2236个,198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又对原来总表中的个别字进行了调整。
二
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汉字简化的方针规定为约定俗成,稳步前进。约定俗成,就是广大群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或认定的使用简体字的习惯。现在看来,这条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汉字简化方案》和总表中的简化字,绝大多数是有约定俗成的基础的,有其稳定性和普遍性。汉字简化使数量可观的常用汉字笔画得到简化,也减少了一定数量的汉字。这次简化基本上是成功的,是受我国大陆的广大群众欢迎的。但是,由于当时推行简化汉字的指导思想存在问题,只是把汉字简化工作当作改革汉字、通向拼音文字的“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吴玉章),变成一种短期的行为,对问题想象得过于简单,好像能较快地实现汉字的拼音化,所以对整理和简化汉字的理论和方法、汉字的学理和系统性、古今贯通、繁简转换、海内外协调、字形的匀称美观等问题缺乏深入细致地科学论证。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所说汉字简化应包括形体和数量两个方面的简化,是很正确的。但也必须看到简化中会产生字形简与明的矛盾,字量过少与对语言的精确表达的矛盾以及某些简化造成自乱系统的问题。求稳的方针是正确的,但分批推行,隔一两年推行一批,会使文字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处在不停变动的状态之中,原有系统破坏了,相对稳定的新系统又形成不起来,这不能不给文字的发展和运用带来消极的影响。1977年12月《第二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布及推行没过多久,即被通知停止使用以至被废止,正是其存在的问题更为突出所造成的。
我们认为,要确定简化字,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条原则:
一、约定俗成。也就是说要确定的简化字在汉字运用的实践中有普遍性和稳定性,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推行的简化字绝大多数都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很多是民间长期流行的俗字、简体字,所以较容易在群众中推行。而“二简”中的一些字有的只在个别行业或某个地区使用,普遍性不强。有的为简而简,是少数人新造的,缺乏约定俗成的基础,所以难以在社会上推行。
二、效率原则。前面说过文字作为一种重要工具,人们会从运用它进行工作的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要求它。选定简化字同样有这种要求,既要求所确定的简化字字形是简易的,笔画少,学和写快而省力;同时又要求跟其他字的区别性强,对语言的表达是明确的,认字和用字确切、方便。
三、规律性。毛泽东主席对汉字简化的指示,强调“找出简化规律”,“有规律地进行简化”,这是很重要的。汉字的产生、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创造、变化一般说来有一定的理据,发展演变有一定的系统性。当然,理据、系统是相对的,汉字的系统性也是在不断发展的,是动态的。经过简化的汉字系统与原来的繁体字系统就有变化。要求文字的发展变化一点也不去变动旧有系统是不正确的,比如,我们不能以《说文解字》系统约束后来的汉字演变,也不能以繁体字系统限制汉字简化。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汉字系统在发展中有传承性,如在原有系统不被打破或较少破坏的条件下一样可以发展到新的系统,还是多一些继承原系统为好。文字的稳定性强,传承性高,有利于文字的运用和对以前文献及传统文化的继承。
三
文改会通过制定汉字简化方案,总结了创造简化字的方法和经验,将简化字划分为八种类型:1、假借字。借用笔画简单的字代替笔画较繁的同音字或异音字,比如脸面的“面”代替面粉的“麵”、山谷的“谷”代替谷子的“榖”,是同音假借;占卜的“卜”代替萝卜的“蔔”、升斗的“斗”代替斗争的“鬥”,是异音假借。2、形声字。指用形声结构造字原理简化汉字,这又有几种情况。A、原字的笔画太繁的形符改为笔画较简的,如刮风的刮-颳、肮脏的肮-骯。B、原字的笔画太繁的声符改为笔画较简的,如袄-襖、衬-襯、础-礎;也有原字的笔画较繁的形符和声符同时都改为笔画较简的,如脏-髒、惊-驚。C、原字的笔画较繁的非形声字改为笔画较简的新形声字,如邮-郵、窜-竄。3、草书楷化字。指将繁体字的行书、草书写法,改为楷书的形式,如东(東)、车(車)、贝(貝)。4、特征字。指用原字的特征部分来代替原字,有的留一角,如声(聲)、医(醫);有的留一半,如录(錄)、号(號)、丽(麗);有的留大部分,如垦(墾)、阳(陽)、际(際)。5、轮廓字。指保留原字的轮廓,省略其中的部分笔画,如卤(鹵)、乌(烏)。6、会意字。指用几个笔画少的意义相关的字或偏旁表示一个意义,构成一个字。如尘(塵)、笔(筆)、泪(淚)。7、符号字。指把原字中笔画繁难的部分,用简单的字与笔画代替,这些字和笔画在字中不表音或义,只起符号的作用。如用“又”的汉、叹、艰、难、欢、观、权、劝、仅、鸡、戏、邓、对,用“不”的还、环、坏、怀。8、偏旁类推字。指运用已简化的字或偏旁类推出来的字。如军(軍)、阵(陣)、连(連)、诨(諢)。
在简化字的八种类型中,草书楷化字,一般为独体字,因为是汉字原有的一种字,这种字可明显地减少字的笔画,又不会增加汉字字数,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办法。但是这种情况在简化字中所占比例很小。特征字、轮廓字、会意字、符号字之类,如果是约定俗成的早已流行的字,既可以减少字的笔画,又不会增加汉字字数,也是不错的办法。但是这几种办法中都还有一些新造的简体字,比如“导、卫、邓、击、严、农、乡、盘”等,作为单字是简化了,作为汉字字数并没有减少,有的打破原有系统性,对学、认有关的字却未必有利。如“盘”,把上半的“般”换作“舟”,少了四画,但汉字中又多了个“盘”字,而且与“般、搬、瘢、磐”失去了系统;“导”字与“道”没有了关系;“邓”与“登、蹬、瞪、簦、凳、磴、镫、澄”系统脱了钩。
下面我们想着重谈谈简化字中形声字和偏旁类推字以及假借字问题。如前所说,简化字中的形声字,是以形声结构的原理进行简化的字。形声字有表音和表意的偏旁,在汉字系统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原有形声字基础上简化偏旁的简化字,既维持了原来的形声结构,又在字形上与原字有较多联系,便于学习和辨认,这种办法比较受欢迎,也是文改主管部门较为注重的一种办法。但是这种办法中无论是代替原来的非形声字而新造出来的形声字还是将原来形声字的形符、声符进行改换形成新的形声字,都是减少了一个繁体字,增加了一个简化字,只是减少了字的笔画,没有减少字数。这与前面说到的几种办法的缺欠是相同的,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偏旁类推字,是运用简化的偏旁或字作为偏旁和部件类推出来的简化字。这种办法简化效率很高,《简化字总表》的第三表就是运用《汉字简化方案》收入的54个简化偏旁和补充规定的9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类推出来了1754个简化字。由于运用了类推简化办法,使得常用汉字中的相当数量的汉字得到简化,也使汉字经过简化整理形成了与原系统有所不同的新的系统。简化字中的偏旁类推字,与前面说的几种办法存在的问题一样,也是只能减少字的笔画,不能减少字数。废除一个繁体字,增加一个简化偏旁类推的字,字数没有减少,在我们的字典里,只要是繁简都收,就得都收下来,比原先没有简化时多收了一些简化字。新造简化字和类推简化字又为我们的汉字总字库增添出来数量可观的新的成员,这与汉字简化的减少汉字总字数的目标是不一致的。
类推简化还有个范围问题。1964年《简化字总表》的“说明”中指出:“第三表所收的是应用第二表的简化字和简化偏旁作为偏旁得出来的简化字。汉字总数很多,这个表不必尽列。……现在为了适应一般的需要,第三表所列的简化字的范围,基本上以《新华字典》(1962年第三版,只收汉字八千个左右)为标准。未收入第三表的字,凡用第二表的简化字或简化偏旁作为偏旁的,一般应该同样简化。”十分清楚,当时的汉字简化工作的主管部门主张类推简化是没有范围限制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辞海》所收汉字都是进行类推简化的,1980年《新华字典》的修订版本又增收了不少汉字,也是同样类推简化的。这些字典、词典收字不过是一万多,多的也不超过两万。八十年代后,我国要编辑出版大型字典、词典,类推简化就突出了。1986年10月,《汉语大字典》开始出版,在其《凡例》中说:“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编发的《简化字总表》所列字目为准。”1986年11月开始出版的《汉语大词典》也在《凡例》中说:“简化字只立单字条目”,“夹注及立目的简化字,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教育部1964年联合发布的《简化字总表》所列的2236个字为限。”也就是说,这两部收字较多的大型辞书(其中《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四千多个),类推简化只限于“总表”范围,以外的不类推简化。但是1994年9月出版的《中华字海》收字85568个,它收字比“大字典”多出三万多,主要是收录了《简化字总表》范围之外的类推简化字,甚至连一些古代的讹字也进行了类推简化。对这两种收录简化字的范围,辞书界也多所议论。近年大型计算机字库的建立,一些古籍的简体字版出版,类推简化的范围问题就更为突出了。我们认为,类推简化不必只限定在“总表”之内,范围可以适当地扩大一些,但也不要毫无限制。是不是可将古今的主要典籍用字弄清楚,把现代地名用字弄清楚,确定个范围。这以外的较为罕见的字,有的只是较专门的古书用到,或者只是古代字书上收录,而古籍上见不到的字,还有的字在字书上也注不出音义的,有的甚至是讹字。一些古代不用现代也不用的字根本不必列入范围,自然更不必类推简化了。也有可能以后还有重要文献出土,需要出简体字本,会有所定范围以外的字,那会是极为有限的,类推简化的范围也可稍作调整的。
假借字问题。用一个笔画简的字替代音同或音近的笔画较繁的字,实际上不仅是替代,而且是兼并。同音代替在汉字发展的历史上就是汉字简化的重要方式。这种办法不仅简化了笔画,而且又减少了字数,这是最为符合汉字简化的目标的,所以它也最受原推行汉字简化的主管部门重视,列为汉字简化的第一种方法,首选的办法。但在文字运用中,这种办法出现的问题较为突出。由于是同音代替,有的还不完全同音,这就给选用的字增加了义,有的还增加了音,就有引起混淆的可能。比如“干”字,近年常见“干细胞”一词,其中的“干”有人读阴平,有人读去声,如不了解术语含义,就难以确定;翻译地名“塔什干”中的“干”,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不止一个人读成去声。再比如,我见到有位经理的名片,全用繁体字,上面的地址“海淀区芙蓉里”中的“淀”印作“澱”,“里”印作“裡”;还有的把“家”字无限制地转换繁体为“傢”字;我买到一本开本很小印装精致《论语》,用繁体字排版,里面当作说话义的“云”,没有例外地全都上面加个“雨”字头印作“雲”;近年出现的“二恶英”一词,因为“恶”是多音字,常用音义是负面的,所以专家们坚持用带“口”旁的“噁”字,简化字表却是把这个字作为“恶”的繁体废除的。这些问题大都是用同音代替或假借法进行简化而字表又没有注释明白造成的。
由于汉字简化已经推行了四十多年,同音代替又是所使用的重要方法,它所确定的简化字基本上稳定下来。我们不可能再去改变很多已经形成的这种由假借关系而形成的简化字,只能到底对个别的同音代替容易产生混淆的繁简关系进行适当调整(如“后(後)、发(髮)、谷(穀)、当(噹)、蒙(濛懞矇)”等),对那些原本通用范围受限制的假借加以说明,以防转换时产生错误(如“干(乾亁幹)、斗(鬥)、淀(澱)、范(範)、里(裡裏)”等)。
参考文献:
周恩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
吴玉章:《关于汉字简化问题》,《中国语文》1955年4期。
李荣:《汉字演变的几个趋势》,《中国语文》1980年1期。
王显:《略谈汉字的简化方法和简化历史》,《中国语文》1955年4期。
高更生等:《汉字知识》,山东教育出版社1982年3月。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8月。
何九盈:《汉字文化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张书岩:《〈研制规范汉字表〉的设想》,《语言文字应用》2002年2期。
王凤阳:《汉字的演进与规范》,《语文建设》1992年4期。
傅永和:《谈规范汉字》,《语文建设》1991年10期。
王宁:《再论汉字简化的优化原则》,《语文建设》1992年2期。
费锦昌:《海峡两岸现行汉字字形的比较分析》,《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5年1月。
投稿方式:
电话:029-85236482 15389037508 13759906902
咨询QQ:1281376279 ;396937212
网址:http://www.xinqilunwen.com/
电子投稿:xinqilunwen@163.com 注明“所投期刊”